对话彭文生、白重恩:过去40年的全球化模式发生改变,逆全球化带来重新调整(组图)
核心观点:
1、过去40年那种全球化的模式,全球统一大市场,金融自由化,一切以效率、以经济成本为导向的一个模式,现在在发生变化。
2、逆全球化实际上是一个渐进或深化的过程,从早期的贸易保护主义到后面超越经济层面、政治层面的因素。
逆全球化带来重新的调整,尤其是因为地缘政治冲突所带来的逆全球化给全球的经济带来很大不确定性。
对于中国经济在全球产业链的地位,大国规模还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3、推进中国未来经济的竞争力,尤其是创新,现在一定要重视消费。
在知识型经济、创新经济时代,消费的角色,和投资比不能说更加重要,但最起码不能忽视,不能把消费看成是简单的资源消费。
4、新的形势之下,人口结构变化,城市化放慢,不像过去快速发展的阶段,再结合逆全球化,对过去所谓的出口导向型企业确实带来竞争压力。
这个不是今天出现的,实际上过去十几年已经很明显。但如果从结果来说,它不一定是个坏事情。
5、绿色转型本质上是制造业问题,这个对全球的产业链、全球经济未来的发展都有非常重要的含义。
我们能不能维持这个制造业优势?实际上我们有一个很根本性的优势,就是规模优势。
6、(出口)三大件可能会对其他国家产生一定影响,我们要未雨绸缪,跟别人更好合作,实现共赢。
8月23日, 在华尔街见闻创制,中信出版集团、中金公司、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联合呈现的「大国产业链」系列对话中,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部负责人、中金研究院院长彭文生和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白重恩分享了对新格局下宏观与产业趋势看法。
以下是华尔街见闻整理的他们对话的精彩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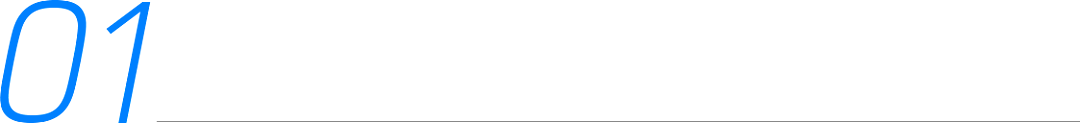
过去40年的全球化模式正发生变化
华尔街见闻周宏: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叫做大国产业链,这是一个大家关注且影响深远的话题,请彭总分享下关于产业链的认知和信息。
彭文生:新冠疫情对全球产业链造成了很大的冲击,虽然现在似乎恢复正常,但是过去几年是让我们对很多过去的问题重新思考的一个很大的冲击。
同时我们在技术层面有一个重要的发展——数字经济,也是越来越受到大家的重视。大家可能都听到数字产业化的一些表述,显示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还有重要的影响。
另外一个就是全球经济正在经历的一个重要转型——绿色转型,对全球产业链也有重大的影响。这是从技术和经济基本面的角度来讲。
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是过去40年的全球化,现在面临所谓的逆全球化,当然逆全球化表述有些争议,有些人可能不太同意这种说法,但是不管怎么样,过去40年那种全球化的模式,全球统一大市场,金融自由化,一切以效率以经济成本为导向的一个模式,现在在发生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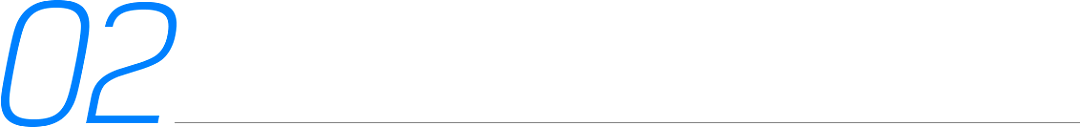
逆全球化不断深化,从经济层面到政治层面
华尔街见闻周宏:过去40年中,全球范围内推动经济市场化和金融自由化的政策主导了全球产业链的扩张,这一趋势在受到逆全球化影响后,会出现怎样的变化和趋势?
彭文生:回顾过去40年的全球化,我觉得有两本西方人写的书值得重视:一是美国政治学者福山在80年代末写的《历史的终结》。
历史的终结是什么意思?过去人类的历史往往被认为是政治,甚至是暴力、战争等不好的因素来决定资源的配置。福山说,过去的历史翻过了,我们现在进入一个新的世界,新的世界是什么?是自由,是市场经济来配置资源。
另外一本是《世界是平的》。过去世界上空间的距离不仅体现在运输,还体现在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文化、价值,还有其他各种因素的限制。
全球实际上不是一个大市场,它在空间上有距离。这本书讲的是空间上的距离没了或者大大缩小,现在就是一个全球的大市场,在这个大市场里我们进行经济活动。这样的全球化是以经济效益成本最小化、效率最大化为导向。
这样的状况,现在遇到两个方面挑战:
美国次贷危机、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已经开始,到特朗普时代就更加突出的是贸易保护主义。这种逆全球化是一个经济层面的不公平。
到后面的逆全球化,在过去几年体现为更多的是安全层面,安全层面又有两个维度。
一个是新冠疫情带来的影响,比如担心因为新冠的冲击,东西都是进口,到时候因为疫情,国外的生产可能停顿下来,跟不上了。这个级别是稳定或者安全。
另外一个影响更深远的是地缘政治层面的安全,我的商品供应可能来自于和我们不友好的国家或政治上的竞争对手,就会担心不稳定、不安全。
所以逆全球化实际上是一个渐进或深化的过程,从早期的贸易保护主义到后面超越经济层面、政治层面的因素。
现在超越经济的或非经济因素的竞争,这和过去 40年我们所熟悉的全球化很不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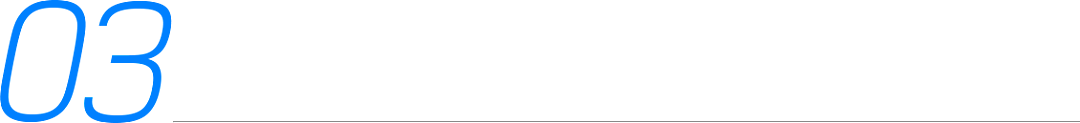
逆全球化带来重新调整
华尔街见闻周宏:在逆全球化的背景下,您认为中国的产业结构和产业链布局发生了哪些变化?
彭文生:从宏观角度讲,两个方面的驱动因素。
一个维度是纵向的,全球价值链有上中下游。
中国和印度处在全球价值链的中下游,或者下游偏多一点,中国现在强调能源安全、粮食安全,从自然禀赋的角度看,我们在下游的位置,必须要搞自主创新。
另外一个维度是横向的,现在有些西方国家讲的去中心化。
所谓去中心化,就是把部分产能移到它本土,或者它认为较友好的国家。
我们的产能,虽然技术不那么复杂,过去规模经济的优势使得产能在中国较多,现在都面临这些问题。这是横向维度,我们面临的挑战。
长远来讲,如果超越全球人类统一大市场的角度,从国家之间竞争的角度,可能也不一定是坏事情。一个国家资源有限,你不可能什么都做,不可能既做技术创新,也做中端、低端制造业,你只有那么多人和资源,所以逆全球化带来重新的调整。
白重恩:逆全球化,尤其是因为地缘政治冲突、地缘政治考虑所带来的逆全球化给全球的经济带来很大不确定性。
我们企业做投资时,不确定性是特别重要的因素,对全球企业都会带来这样的问题。这个不确定性会对全球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对中国宏观经济影响也会很大。
另外,我们现在补短板很重要,但是也希望不能过度地强调补短板,有的时候这种安全是一个很动态的东西。
如果你把所有资源都用来强调补短板,而不去做探索式的创新,那么未来别人在做探索式新创新,新的短板又出来了,我们又要去补短板,总是跟着别人后面追。
所以要有一定的平衡,一方面在补短板方面要做出努力,另一方面要为探索性创新留下充分的空间,未来发展是靠后面这一块。前面这一块是解决当下遇到的问题,而未来的发展是靠后面这一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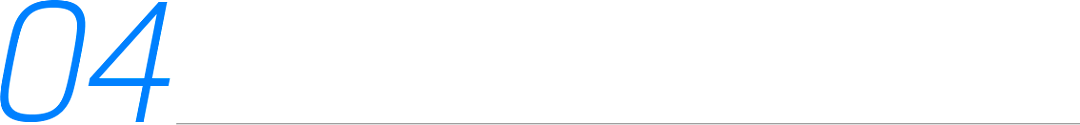
推动中国未来的竞争力靠什么?
扩大消费,促创新
华尔街见闻周宏:中国经济的需求特点和结构对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历史和未来的位置有什么影响?
彭文生:中国经济在全球产业链的地位,大国规模还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规模经济是经济学最经典的一个概念,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讲分工,其实分工和贸易就是实现规模经济的载体。
过去大家较多重视中国供给侧的、生产端的规模经济,这个很直观。比如一年生产10万辆车和一年生产100万辆车,固定成本的分摊是不一样的,生产100万辆车的单位成本就是低。
这也是为什么在技术非障碍的前提下,几乎所有东西在中国生产就是比其他国家便宜。不是因为中国劳动力便宜,我们已经过了那个阶段,而是因为中国的规模经济。
我们思考未来经济发展,还要重视需求端的大市场。人的欲望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无限的,这种欲望驱动创新,而人的欲望又是多元化,人口越多,消费需求越多元化,才越促进创新。
凯恩斯1930年写了一篇经典的文章,提到子孙后代的经济和生活水平,他有两个重要预测:一个是效率大幅提升,另外一个是因为效率大幅提升,人们可以更多享受休闲的生活,每周只要工作两三天。第一个预测符合现实,第二个预测没有实现。为什么没有实现?因为人的欲望是无限的。
需求侧,大国的或人口众多所带来的多元消费需求是驱动创新的最根本动力。生产端的规模经济最终还是来自于需求端(人口、消费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推进中国未来经济的竞争力,尤其是创新,现在一定要重视消费。
在知识型经济、创新经济时代,消费的角色,和投资比不能说更加重要,但最起码不能忽视,不能把消费看成是简单的资源消费。
新形势下,中国未来的竞争力来自于什么?就是通过政策支持促进中国的消费规模,让老百姓能够有支付能力去消费,消费市场的扩大以及多元化是促进创新的根本来源。
白重恩:创新可以有推动,我有什么技术推动创新,也可以有拉动,我有什么需求推动创新。两边都很重要,拉动非常重要。
从推动角度上来说,要想好我们有什么重要特色。在创新方面,从 0 到1是重要的创新,我们现在还不占特别大的优势,未来希望更多;从 1 到 n 也是创新,把一个原始的想法变成产品,再把产品更加高效的生产,生产的质量更好,生产工艺不断地改善,需要很多很多创新。
中国的企业,我们的资源禀赋,就是受到较好教育的工程师很多,全世界最多。这些人可以为我们这种从1到n的创新提供特别大的支持,中国在这方面有非常独特的优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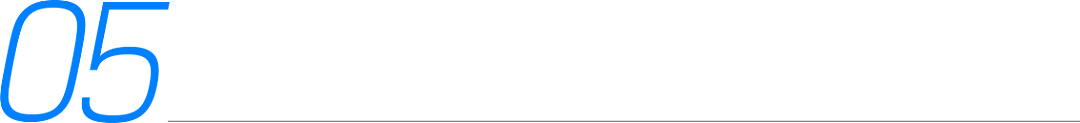
出口导向型企业虽有压力,但未必是坏事
华尔街见闻周宏:中国出口导向型的企业在全球产业界价值链的参与中会受到什么挑战?它可能有什么样的取向帮助它更好的度过这个挑战?
彭文生:出口导向型企业有一定过去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或者历史的原因。比如过去人口规模红利阶段,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从农村转向城市,城市化过程中,我们本身储蓄率高,意味着我们产品就是要出口,自己消费不足。
新的形势之下,人口结构变化,城市化放慢,不像过去快速发展的阶段,再结合逆全球化,对过去所谓的出口导向型企业确实带来竞争压力。
这个不是今天(才出现),实际上过去十几年已经很明显。
但如果从结果来说,它不一定是个坏事情。它反映了我们现在出口占经济的比重下降,可能是经济本身更深层次的基本面因素(人口、城市化)和其他因素所决定的。这是从事后看,它不一定是个坏事情。
但是从事前看,不是光看结果,而是看经济的对外开放度。我们的企业是不是参与全球市场的竞争,从这个角度讲,它又非常重要。
参与全球市场竞争对提高效率、促进创新非常有帮助。为什么这样讲?
比如一个经典的事实:新兴市场国家成功地实现经济腾飞,往往都是体现为什么?制造业体现为出口。
制造业出口,参与全球市场竞争,必须靠质量、靠降低成本、靠提高效率,才能赢得市场。靠垄断、靠寻租、靠权力寻租,靠其他的,那必然就会损害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比如房地产行业过度扩张,因为它天然是一个垄断的行业,不利于效率提升。
还有一些国家叫资源诅咒,实际上不利于经济发展,为什么?因为资源往往带有垄断属性,是政府给你牌照,这个牌照的获得可能不是市场充分竞争的结果。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维持一个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或者维持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对我们未来发展非常重要。
白重恩:我们企业全球化的能力还需要加强。企业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有它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环境,能不能适应好?这是中国企业需要补的重要一课。
我们现在需要走出去,绕过各种各样的障碍,但是否有能力这样去做,这是我想说的一个方面。
另外,我们体量大。当我们在某个产业做得很好时,出去对全球的冲击会很大。过去我们已经有这样的情况,未来仍然会有这样的情况。
现在出口还很顺的企业,要考虑,比如现在所谓的新三件——新能源汽车、电池、太阳能电池——出口增长很快,生产能力又这么强,会不会给出口目的地国家带来比较大的冲击,从而产生反弹?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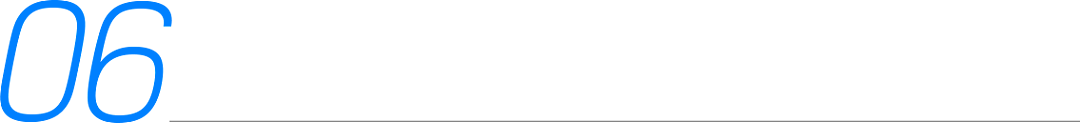
绿色转型本质是制造业问题,中国要发挥最根本优势
华尔街见闻周宏:ESG和绿色转型对中国经济未来和全球产业链的地位,有何影响?能起什么作用?
彭文生:可以从两个视角来看,一个是从结果来讲,一个是什么样的政策来促进这个结果的实现。
从结果来讲,所谓绿色转型实际上就是要从传统的化石能源转化为可再生能源,或者叫清洁能源。
那什么是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氮,氧,风已经存在,关键是我们通过什么样的设备和技术,把它有效的、低成本的利用起来。
从这个意义上讲,绿色转型本质上是制造业问题,这个对全球的产业链、全球经济未来的发展都有非常重要的含义,因为能源是经济的基础。
最根本的从结果来讲,制造业会更加重要,能源也变成一个制造业。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实际上对我们是有利的,无论是从效率、安全,还是国际竞争的角度来讲。我们如果能够维持制造业优势,绿色转型对中国是有利的,效率和安全都有利。
我们能不能维持这个制造业优势?实际上我们有一个很根本性的优势,就是规模优势。
中国人口现在可能是第二大,和第一大印度差距不大。此外,我们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超过2亿,印度和美国都不到1亿。这些因素都意味着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在绿色转型中间占有优势。
那怎么把这个优势发挥出来?其实绿色转型和公共政策有关系。绿色转型涉及碳排放,有很强的外部性。要是没有政府政策干预,靠纯粹的所谓市场主体的行为,那它(市场主体)觉得用天然气、煤炭挺好的,成本挺低的。所以需要一些(政策干预),包括产业政策。
过去我们以西方为主导的绿色转型,他们强调需求侧,怎么样限制化石能源的需求,所以看定价和交易市场,不能说它不应该,但是以前可能过多强调了需求侧。
中国在新能源领域形成了一些优势,实际上是从供给侧来入手的。我们是扶持产业,扶持太阳能、光能产业,这是另外一个手段。当然这两个可能都要结合起来,但是中国的优势在供给侧,实际上和我们制造业优势相辅相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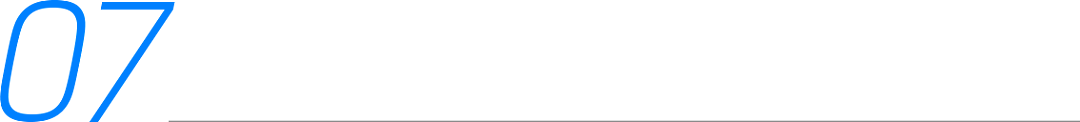
出口三大件可能对其他国家产生冲击
白重恩:我们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制造能力很强,但是在使用方面,比如新能源的发电占发电的比重尽管在增长,但还是不高。那么一个很重要的制约条件就是整个电力体系下消纳能力不够,这成了一个制约因素。
要增强下消纳能力,需要从两个角度去考虑:
第一个,提升消纳能力的基础设施。因为新能源供给不是很稳定,那么要和其他能源的供给、需求侧的响应配合起来。所谓需求侧响应,是希望在太阳能发电多的时候企业多用电,在太阳能发电少的时候企业少用电。另外除了这个需求侧响应,还有储能和调峰的能力。
第二个,让市场机制起更大的作用。要让我们的价格体系能够推动能源的使用者来自我进行峰谷调节,用价格体系来鼓励人们投资储能和调峰。
中国在绿色产业方面做得很好,但是也有短板——在消费领域,消费者的绿色意识还不够强。我们给消费者提供激励也不够。
另外有一些新的比如氢能的利用,其他国家也有特别好的技术,也要虚心向别人学习。
最后,三大件可能会对其他国家产生一定影响,我们要未雨绸缪,跟别人更好合作,实现共赢。








 +61
+61 +86
+86 +886
+886 +852
+852 +853
+853 +64
+64


